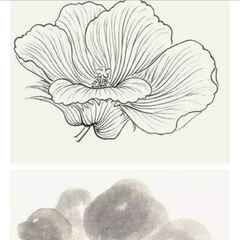作者:吕叔湘
我认识圣陶先生是在成都 ,1941年春天的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那时候我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 , 圣陶先生 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 教育科学馆计划出一套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参考书。 其中有一本 《精读指导举隅》 和一本 《略 读指导举隅》 , 是由圣陶先生和朱佩弦先生合作编写的。 计划里边还有一本讲文法的书 , 圣陶先生从顾领刚先生那里知道我 曾经在云南大学教过这门课 , 就来征求我的意见 , 能否答应写这样一本书。
我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 , 跟我想象中的“文学家”的形象全不一样 ; 一件旧棉袍 , 一把油纸雨伞 , 说话慢言细语 , 象一位 老塾师。 他说明来意之后 , 我答应试试看。又随便谈了几句关于语文教学的话 , 他就回去了。 那时候圣陶先生从乐山搬来成 都不久 , 住家和办公都在郊外。过了几天 , 他让人送来一套正中书局的国文课本 , 供我写书取用例句。
大约半年之后 , 我写完了《中国文法要略》的上卷 , 送给圣陶先生审阅 , 那时候他已经把家搬进城里了。后来开明书店 设立成都编译所 , 就设在圣陶先生家里。圣陶先生一直在主持《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 后来又跟宋云彬先生合编《国文 杂志》 , 他邀我给这两个刊物写稿子。我的《文言虚字》 、 《笔记文选读》 、 ’ 《中国人学英文》以及《石榴树》 (即《我叫阿 拉木》 ) 的译文 , 或全部 , 或部分 , 都是在这两种刊物上发表的。因为送稿子到圣陶先生那里去 , 也就常常留下来 , 一边说着话 , 一边看圣陶先生看稿子。圣陶先生看稿子真是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 , 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笔误 , 理顺作者的语句 , 甚至 连作者标点不清楚的也用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的时候也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 , 但是我知道 我赶不上圣陶先生。
写《中国文法要略》以及《文言虚字》等等 , 是我对学术工作的看法有了变化的表现 , 哪是因哪是果可说不清。原先 我认为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 , 深而又深 , 普及工作是第二流的工作。我自己思想中本来就有这个倾向 , 我在那里工 作的研究所的主持人更是十分强调这一点。可是我现在认识到普及工作需要做 , 并且要把它做好也并不容易。回想起来 , 我确实是受了圣陶先生的影响。圣陶先生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编《中学生》 , 值得吗 ? 非常值得。现在七十多岁 到五十多岁的人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中学生》的忠实读者 , 在生活上和学问上是受过它的教益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个故事。 1949年初 , 开明书店收到魏建功、萧家霖等几位先生从北平寄来的编字典的计划 , 圣陶 先生认为这个计划很好 , 复信说开明可以接受出版。这就是后来由附设在出版总署内的新华辞书社出版的《新华字典》 , 那时候圣陶先生任出版总署副署长。 《新华字典》出版之后 , 新华辞书社并没有解散 , 圣陶先生打算让这个班子继续编别的 辞书 , 并且希望建功先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 , 继续领导辞书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 , 态度很坚决。后来有一天圣陶先生 跟我闲谈 , 谈起这件事 , 他说 :“难道在大学里教课一定比编字典的贡献大吗 ? ” 现在建功先生和圣陶先生都已经作古 , 我也不 需要保密了。
1945年 , 抗日战争结束 , 圣陶先生一家随着开明书店由长江出川回上海 , 第二年我也随金陵大学回南京。为写稿的事 , 也时常有书信往还。 1947年 , 圣陶先生约朱佩弦先生和我参加高中国文读本的编辑工作 , 我建议把语体文和文言文分开 , 编 成两套 , 他们两位都同意。到 1948年冬天 , 淮海战役的胜负已成定局 , 南京城里人心惶惶 , 很多人家避居上海 , 我也扶老携幼 投奔开明书店。我在开明书店工作了一年有余 , 认识了章锡深、王伯样、顾均正、徐调孚 , 贾祖璋、周振甫、唐锡光等“开 明人 , ’ , 也多多少少感染上了那难于具体描写却确确实实存在的“开明作风” 。圣陶先生不久就去香港转道去北京参加政 治协商会议 , 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 第二年我应清华大学之聘也来到北京。 虽然住得不近 , 也还时不时有 机会见面。
1951年 2月 , 我母亲在上海去世 , 我奔丧回南。 回到北京 , 家里人告诉我 , 圣陶先生找过我 , 说有要紧事儿。 我去了才知 道是要写一个讲语法的连载 ,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 主要是供报刊编辑以及一般干部参考。发起这件事的是胡乔木同志 , 他曾经问过语言研究所 , 语言研究所不愿意承担 , 才找到圣陶先生 , 圣陶先生说可以找吕某人试试。这就是《语法修辞讲话》 的由来。这件事在我的生话中形成又一个转折点。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时候 , 我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 , 做语法研究 工作 , 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兼任一名副总编辑 (圣陶先生是社长 ), 照料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如果没有《语法修辞讲话》这 件事 , 很有可能我会跟着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 , 或者调到别的大学去。
《语法修辞讲话》给我惹出许多事儿。首先是到处邀请做报告 , 其次是回答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过了几年 , 好象没 事儿了 , 忽然有一天接到圣陶先生一个电话 , 说是某方面的指示 , 要写一篇批判《语法修辞讲话》的文章 , 并且点名要圣陶先 生写。圣陶先生在电话里说 , 这篇文章他不会写 , “解铃还是系铃人 , 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吧。署名当然还是署我的名字。 ”这 可把我难住了。对于 《语法修辞讲话》 我也不怎么满意 , 可是我的不满意跟那位不知道名字的发指示的同志的不满意 , 大概 不是一回事。 所以这篇文章很难写 , 既要让考官满意 , 也得让挨批者不太难堪。 好在已经过多次政治学习 , 如何发言才算 “得 体”已经多少有些经验。饶是这样 , 一千多字的文章还是写了一个星期 , 登在《人民日报》上 , 也不知道命题人是否满意。 《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引起了一阵“语法热” , 一两年内就出版了十来种语法书。圣陶先生大概也看过几种 , 好象 都不满意 , 有一天跟我说 :“能不能写一本不用术语的语法书 , 容易懂 , 而且实惠 ? ”我说 :’ ’不用术语恐怕办不到 , 少用几个 , 象 `名词 , 、 `动词’ 、 `主语’ 、 `谓语’等等 , 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实惠 , 也就是对说话、作文有帮助 , 那就更难了。 ”圣陶先生 当然没有叫我试写 , 我可偷着试过好几次 , 都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希望有人能满足圣陶先生这个遗愿。
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照料初中汉语课本的编辑工作 , 当时的计划是要把汉语和文学分成两套课本的。实际工作是张 志公同志负责 , 但是我得认真审读 , 提修改意见。这套课本仅仅试用两年就不用了 , 汉语和文学又合流 , 恢复原先的语文课本 的编法。 这时候我已经不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职务 , 但是圣陶先生叮嘱我好好审读新编的语文课本。 不久 , 我在语言研究所 主编的 《现代汉语词典》 的初稿陆续出来 . 圣陶生先和朱文叔先生都是审订委员会的委员 , 也只有他们二位认真提了些修改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 彼此不通音问。我听说周总理设法保护文教界的一些老先生 , 估计圣陶先生会在内 , 也就 放心了。我自己则由隔离反省而集中学习 , 而下干校 , 又和二十多位同志于 1971年初提前放回北京 , 仿佛做了一场希奇古怪 的大梦。 这时候虽然仍然受驻机关的军宣队、工宣队管束 , 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动 , 于是有一天我就去访问圣陶先生。大 概这个时候圣陶先生那里还是很少有客人来吧 , 看见我非常高兴。 寒暄几句之后 , 他睁大眼睛问我—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你是什么罪名 ? ”我说 :“反动学术权威加走资派 , 双料打倒对象。 ”圣陶先生叹了口气 , 半晌不说话。后来互相交换熟人 的消息 , 圣陶先生扳着指头算了会儿说 :“我认识的人里边 , 死了的和下落不明的 , 十七个。 ”
圣陶先生和王伯祥先生是幼而同学 , 长而共事 , 交情很深。伯祥先生那时候身体不好 , 在家里很寂寞 , 圣陶先生常常去 看望他 , 有时候乘公共汽车 , 有时候步行。二位老人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此 , 我也过些时候就去看看圣陶先生 , 尽管没有 多少话要说。
叶圣陶先生不是以书法知名的 , 可是书以人重 , 来求墨宝的还是很多。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得到他一副篆书短联。 1976年有人送我两张高丽棉纸 , 我拿去请圣陶先生给我写点什么。他写了两首诗送我 , 是楷书写的。
华西初访犹如昨 , 既接清芬四十年。 邃密深沈殊弗逮 , 斌存虚愿欲齐贤。 并臻信达兼今稚谓使用现代语 , 译事群钦夙 擅场。颇冀移栽名说部 ,`卑因橡笔得深赏。
这里既有溢美之辞 , 也有勉励的话 , 希望我翻译外国名著。我又何尝不想在这方面多做点工作 , 但是我也跟很多人一 样 , 时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 , 也就顾不上了。
在这以前 , 圣陶先生也曾经在我女儿吕霞写的《在抗战中度过的童年》的前边题过一首《洞仙歌》 , 那些短篇是原先 发表在《开明少年》上 , 后来剪贴成册的。
华西初访 , 记见垂髻觑 , 小试文心不吟絮。叙离乡 , 辗转汉浦湘奉 , 更绕道遥傍滇池侨寓。晨曾摊手稿 , 开载于今 , 重读依然 赏佳趣。观感本童心 , 暗喜轻愁带幽默 , 时时流露。待掩卷津津味徐甘 ,
却不免追怀西南羁绪。
1977年 8月 , 谢刚主 (国祯 ) 先生发起去承德避暑山庄游览 , 邀请圣陶先生、唐搜同志和我同去 , 圣陶先生由至善世兄 随侍 , 唐恻同志和我也都有家属陪同。那时候避暑山庄还没有正式开放 , 游人很少。我们住在文津阁楼下 , 非常清静。早晚 在松林中散步 , 虽少花香 , 不乏鸟语。尽管只住了一个星期 , 但是来去自由 , 没有多人迎送 , 也不要讲话和应酬 , 圣陶先生 心情很舒畅 , 后来还屡次提到。第二年夏天圣陶先生参加政协的视察组去四川 , 路上患病 , 回到北京去医院检查出来是胆结石 , 做了手术 , 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 , 健康大受影响。这以后 , 除 1982年到烟台作短期旅行外 , 就没有再出京了。
我最后一次晤见圣陶先生是 1987年 9月 8日。这一年他的健康情况比较稳定 , 那一天正好有新华社的老摄影记者邹健 东同志来给圣陶先生拍相片 , 也给我们两人拍了一张合影 , 圣陶先生兴致很好。 H 月 17日上午我去看望圣陶先生 , 他因为晚 上没睡好 , 早餐后又睡着了 , 我没有惊动他。至善有事出去了 , 我跟满子说说话就出来了。后来我自己闹病 , 住了一程子医院 , 回家休养 , 一直想去看圣陶先生都因循未去。有一天张志公同志来看我 , 说起圣陶先生 , 他说他也好久没去看望了。我们相 约过几夭去看他老人家。又过了几天 , 志公在电话里告诉我 , 圣陶先生又住院了。最近几年 , 他常常住院 , 所以我也没放在心 上 , 打算过些时到医院去看他。二月十六日早晨 , 志公同志来电话 , 说叶老去世了 , 我后悔没早去医院。第二天我自己患感冒 躺下了 , 追念往事 , 做了一副挽联 :
交情兼师友 , 四十八年 , 立身治事 , 长仰楷式。
道德寓文章 , 一千万字 , 直言曲喻 , 永溉后生。
也只是在心里念道念道 , 没有写出来送到民主促进会举行的追思会上去。下联是天下的公论 , 上联却是说出我个人的感 受 , 可是我相信 , 象我这样受过圣陶先生言谈的影响、行事的感染的真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啊 !
文体: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