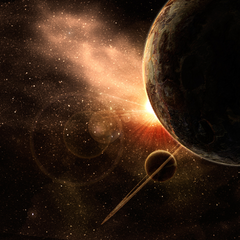作者:鲍鹏山
孟子是“亚圣”。从学问渊源上讲,他也算是孔子的嫡传。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而子思又是受业于对孔子思想“独得其宗”的曾子,这就显示出孟子的正统地位了。这正统地位,连野心极大用心极深篡位之欲极强的唐代韩愈都不敢有任何微词。韩愈可是攻坚拔固的好手,他一路势如破竹地向历史进攻,连荀子都给他推翻了,并踏上一只脚。但到了孟子跟前,也许看看孟子太强大,自己确实不是对手,也许自己已是强弩之末,只好打不赢就招安,马上变出温驯之色,对之顶礼膜拜,并在孟子身后给自己“敷座而坐”,擦擦头上的虚汗,摆出一副自我作古的派头,俨然在道统中有了一席之地。
但孟子的“亚圣”地位,是不靠嫡统,不靠韩愈式的自封,而是靠他对儒门的大贡献。可以这样说,在孔门的历代弟子中,数孟轲先生最为有斗志,有干劲,有热血,而又最无私心,无渣滓心,无势利心。一句话,最无“小”心。
孟子之“义”
孔子谈“仁”也谈“义”,孟子谈“义”也谈“仁”,但两者还是有侧重点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义”,所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仁”“义”区别在哪里?其实两者本质并无不同,只是表现的地方不同。孟子就进行过区分,他说:“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仁,是人的内心修养,义,是人所遵循的正道)他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是人安身立命之所,义,是人行事的正确法则)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义”,表明他更注重对人外在行为的评价,这除了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现出来,施及于人,也表明他更注重实际—— 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我们是无从知道的,也无须知道,无须控制也无从控制,只要他外在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即可。所以,“义者,宜也”(义,就是行为适当)。所以,孟子的“义”比孔子的“仁”,更具体可行,操作性强。同时,“义”的评价比“仁”的评价也可行得多。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义”(适宜),总比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
义,对道德实践者而言,也便于操作。要真正地在内心意志上达到圣人的境界谈何容易?但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说,在内心的欲求与“义”发生矛盾时,能克制自己而屈从“义”,则较易做到。孟子可能是意识到,要求人人都有一颗圣贤之心,实在是一种妄想,现实一点的是,要人人都能对自己有所约束。应该说,孟子走的这一步,是使得不可企及的孔子人格理想走向大众。大众不可能人人在事实上成圣,但大众可以通过自我约束,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孔子的“圣贤”理想只能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追求,而孟子的“义”则有可能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
如果说,孟子把孔子的“仁”从道德角度发展为“义”,那么,从政治角度,他又将之发展为“仁政”,也就是他的“王道”。在这一点上,孟夫子可是为儒家学派立了大功。孔子也讲过“仁政”,但对其内涵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显得空洞而浮泛,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是孟子接过手,把这工作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得承认,他做得蛮出色。他把孔子的伦理思想演义为一整套的政治构想,完成了由学术向政治的过渡,学者成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为“王者师”。
这套理论,使得学统、道统与政统融合无间,从而“学”与“仕”不再有任何学理上的隔膜,“学而优则仕”变成了“直通车”,“士”变成“士大夫”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说孟子的“融合三统”不是为后来的科举取士奠定了基础呢?
孟子之“性善论”
孔子不愿意谈人性,他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论语》中只模糊地提到“性相近,习相远”,只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并未做善恶之分。所以,从这一点讲,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都与孔子不矛盾。但孟子的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基础。在这一点上,孟子对儒家可谓功勋卓著。后来程朱等人严厉批评荀子的性恶论,并藉此认定荀子已失去儒家的根本,他们也算明白人,知道在性善问题上决不能作丝毫的让步,因为这一步让出去了,儒家就没有立锥之地了。但非常令人为儒家担心的是,孟子在他的七篇大作里并没能证明“人性善”。傅伟勋先生在他的《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一文中,列出孟子证立“性善论”的十大论辩,指出,这十大论辩都不能直接证立“性善论”。既如此,那就不管数量多少也没用了。十个不完全的论证,不能凑成一个完全的论证。一百个也不行,一千个一万个也不行。这会令今天的新儒家着急,但着急也不行。
可以说,在对人性本善的论证上,聪明绝顶的孟子已经绞尽脑汁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利用的都利用了,以致后来的程朱们再也不能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能在那里发一些空洞的欢呼。像程颐和朱熹,就喜欢故作高深地发些大可不必的感慨,常常在《四书》的某些字缝里写上什么“学者宜深思”字样——他们说不明白,就叫我们去深思,可我们想来想去也就那么一点意思。而就为这点没有什么意思的小意思,我们一代一代毫无出息地老去了。
我想,人性问题,无论是证善,还是证恶,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不能证明的问题。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比如用“恻隐之心”来证明人性本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触动恻隐之心的经验,好像其普遍性足以证立人性本善。但是,我们是否也普遍具有“小人之心”的经验呢?比如妒嫉、幸灾乐祸、争夺等等呢?
既然我们不能证明人性善或恶,那我们可能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作价值层次上的选择。孟子就是这么做的。他已被自己的证明搞得焦头烂额了,还不如趁早摊牌,获得解脱。他有一句话,表明他认定性善,乃是出于价值考虑而非事实认定。这句话是:“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他的意思是,你若说人性不是善的,那么人要是做了坏事,并安心于做坏事,且声称这是出自人的本性,你有什么理由制止他呢?唉,这位天真迂阔的孟夫子,他竟幼稚到想用道德激励的方法来防止罪恶!后来,我们也就这么干了。我们喊几声“皇上圣明”,心里并不认为那个憨大真的圣明,而是想借此鼓励他变得圣明一些;喊“皇上仁慈”,也并不认为那凶恶的家伙真的仁慈,而是想借此使他不好意思凶恶。噫!当我们认定性善,撤去一切自我防范,把一切都交给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皇上后,我们除此之外,能有其他什么法子吗?谁让我们撤除了对权力的戒备呢?是“人性善”呀!所以我们也只有等待着君主们偶一良心发现,像爱惜一头牛一样爱惜我们了。
孟子式人格
孟子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这一点不比孔子,孔子坚如磐石。最早批评孟子的是荀子,这位和孟子同在稷下,同尊孔子的后辈好像和孟子有些过节,他对孟子的批评非常地感情用事,很有一些泄私愤的味道,与他一贯的公允平实大相径庭。到东汉更有王充,用极为刺眼的《刺孟》来刺他。不过,总体而言,荀子批孟乃学术之争,颇有创见;王充《刺孟》虽然不免强辞夺理,乱刺一通,但他的着眼点仍在寻孟子的逻辑错误与言行矛盾,并还真的找出了一些孟夫子在夸夸其谈时犯下的错误,对我们颇有启发。而后来的一些卫道士对孟子的批评就不同了,他们批评孟子,不是学术之争;相反,他们对孟子的那一套政治构想是无条件赞同的,他们批评的是孟子的人格。在与君主的关系上,孟子“大丈夫”气太足了,使乐于做妾并做出甜头的他们颇为心烦。比如程颐,他赞孟子“仁义”,赞孟子“养气”,赞孟子“性善”,赞孟子“以道自任”,一路赞下来,却在另外一处停了下来,瞧来瞧去不顺眼,嗅来嗅去不是味:“孟子有些英气”——他说对了;“才有英气,便有圭角”——他又说对了。大凡走狗,鼻子是第一位的;大凡做妾,善伺颜色是第一位的。“英气甚害事”——害什么事呢?照他的意思,当然是害成圣成贤之事。但我还是戳穿了他说,害成妾成臣之气。我读程朱的文字时总是全身不舒服。我不知道明代的读书人是如何受用的。我要是在明代,我还是去做贩夫走卒的好,而决不能去参加科考——参加科考得读程朱呀!
孟子有英气,英气勃发,那是丈夫初长成时的阳刚之气、浩然之气。孟子有圭角,凛然难犯,那是男儿的铮铮傲骨,无一丝邪媚之态。这正是孟子最了不起的地方。而程颐,照他看来,孟子若去掉英气,磨去圭角,圆滑邪媚,又酸臭冬烘,像他那样整日龟缩在一己的养性斋中做所谓的道学,养所谓的心性,对天下汹汹罪恶装聋作哑,以麻木不仁为圣贤气象,以无同情心无良心为修成正果,那才算是成了圣。成了“圣”吗?是成了“妾”吧?那个程朱的道学,我越看越像“妾学”。“妾妇之道”是什么呢?孟子早就说过了,点破了:“以顺为正”!“以顺为正”了,还能有英气吗?所以他不愿意顺,所以他不做臣,他要做“王者师”,王者若不认他这个师,他就做独立的大丈夫。不吝去留,了无牵挂,就是不做委身事人的臣妾。
李贽曾倾心赞美齐宣王为“一代圣主”,这个意见我也是同意的。至少从胸襟气度上讲,古往今来,比得上他的还真没几个。让一帮人在他身边“不治而议论”,专挑他的不是,他还供给这些人很不错的饭碗、别墅和车辆,宣王大矣哉!
宣王的资质秉赋也很不错,所以他成为孟子最好的对话者。哲学往往就是在智者之间的对话中自然生成。不过像孟子那样盛气凌人,党同伐异,一般人是不愿意和他辩论的。他在稷下学宫就好像没人和他辩。他的“好辩”名声太大,而且一辩就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辩论风度极差,一点也不费厄泼赖。甚至辩不过就骂,比如他骂杨墨: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
这种骂法,人们当然对他敬而远之。孟子此时会有独立荒野、拔剑四顾无敌手的寂寞吧。这时齐宣王常派人来请他去聊聊,实在是雪中送炭的。但他偏偏还摆架子,说什么圣君有不招之臣,必须先师之然后臣之,让齐王来见他。他先糊弄出一个理论根据,说人受尊重有三点:年纪大,学问大,地位高。宣王只占了一条地位高,而我孟子占了两条,二比一,当然应该是他来见我。孟子的朋友景丑就责怪孟子说:“我是常常看见齐王敬重您,而从未见过你何时敬重过齐王。”孟子食人之禄却没有一点谀媚之态,反而端起碗吃人酒肉,放下碗骂人爹娘,颐指气使,大大咧咧,如同别人欠了他什么!宣王位尊权重却没有一点蛮横之状,反而恭敬有加,小心翼翼地听从教训,如同犯了错误的学生。这是理想的文人与侯王的关系,也是理想的“道”与“势”的关系。我们算是在孟子那里见着了,就凭孟子让我们开了眼这一点,他也理当受我们三拜。
孟子好骂。他骂杨墨,但他更骂诸侯。他常常骂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顾左右而言他”。对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他好像尤其恼火,一则当面骂梁惠王“率兽食人”(带着野兽来吃人)!这简直是说出了专制君主的共同兽性。“不仁哉!梁惠王也!”再则背后骂梁襄王“不似人君”。他把当时所有的诸侯,一律骂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杀人”。我以为,在先秦,有五种主要的人格理想,其中一种就是孟子式人格,孟子式人格是什么?就是大丈夫!
孟子的这种人格,也是时代的赐予。孟子是他那个时代原野上的参天大树,也仅仅那个原野可以有参天大树。随着专制渐深,能生长的也只有一些“无人知道的小草”了。这些小草没有精神,没有性情,当然也就“没有寂寞,没有烦恼”。时乎!时乎!明太祖朱元璋,就不能容忍孟子。他年轻时不读书,只杀人。待到杀上王位,才开始读书。一读,才知道那大名鼎鼎的在孔庙里配享孔子、受后人祭拜的孟夫子,原来对权势是如此的大不敬!专制魔王大动肝火了,他破口大骂:“这老东西如果生在我明朝,他能免于一死吗?”朱皇帝恨不得把他大明王朝的鬼头刀伸向先秦,去砍杀孟轲。他可能在他阴森森的宫殿中谋算过,要学伍子胥去掘坟鞭尸吧!至少他是把孟子从孔庙中赶出来了,把他的书删节了。我在600年后仍能听到朱皇帝咬牙凿凿,仍能看到他眼中的邪火闪闪,但反过来看,一个人的文章能让千年之后的暴君恶棍如此咻咻不已,肯定是好文章。暴君的切齿声,是对文章的最高评价。
事实上孟子如此大倡民贵君轻,辩才无碍,口若悬河,理直而气壮,气盛而言宜,若在后来大一统的专制王朝,早就祸从口出,断送老头皮了。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去做“亚圣“?